[转帖] 世人闻所未闻的“1967年文革湖南道县大屠杀”
世人闻所未闻的“1967年文革湖南道县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杀中国人,现在看看和平时期中国人是怎样杀中国人的!2014-03-12 编辑: [url=]西安食神会[/ur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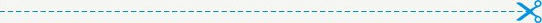
【点击标题下面“西安食神会”关注我们】
【点击右上角,分享微信内容进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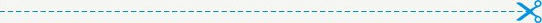
作者:周康伟
永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三皇五帝,舜葬九疑的传说和红军长征过永州的革命历史事件,使永州闻名于世;永州,中国历史的缩影;她是五千年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永州产生过李达、陶铸、江华这样的中共党史人物,永州是秦光荣的故里。
作为永州人,我想一定要弄清永州道县1967年发生的大屠杀事件,湘江上游漂下来的尸首犹如天灾。漂浮着尸体残骸和人类耻辱的潇水河,那既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笔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从零陵到道县,要翻越双牌和道县之间的山-----单江岭,属南岭山系五岭之一的都庞岭山脉,俗称螺丝岭,其实它的正式名字叫阳明山,但阳明山范围很宽,这单江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山里有个林场,叫打鼓坪。
单江岭,永州南北分界岭,由此分成南六县,其中道县都庞岭下一个荒僻落后的小县,有一条出名的濂溪河从那里流过,它是以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字而命名的。改革开放以来道县一直想做这个区域的中心,在拼命争夺势力范围。
在道县大屠杀中,被杀的人大多是满门抄斩,有的大队甚至株连族人。被杀的人大部分是当时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最后派了军管,才平息下来。
屠杀的方式骇人听闻:用自制的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集体轮奸后杀害。
据全道县统计,屠杀的方式共有一百零八种。基本归纳为10大项∶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7、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8、绳勒(含勒死和吊死)。9、火烧(含熏死)。
有的被杀人团作为反革命一齐赶下岩洞,摔得半死,然后活活饿死闷死在岩洞里,凄厉惨烈的哭叫声持续达两天两夜,令人闻之丧胆。洪塘营公社的杀人团,把两百多名反革命绑到附近的矿坑旁边,杀人团的李波清等先用枪打,然后不管死活,一律推下矿坑活埋。
桥头乡桥头村右派周文楝及妻子陈莲娥、子周辉在杉木岭出工时,被生产队长指挥青壮劳力,推进一囗多年不用的废窖里。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囗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
杀人凶手们不但杀父奸女、杀夫霸妻,还对受害人妻女进行集体轮奸。杀人凶手不仅是为了执行任务,还为了从中获取报酬。在大屠杀风潮中,当时的“行情”是:每杀一人,报酬一般是二、三元或10斤谷不等,酬金由大队或公社开支。
文革时期,道县的夺权斗争是在两个人中间进行的。一个是道县县委书记石秀华,一个是县委副书记熊丙恩。一月夺权风暴后不久,石就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靠边站了。熊丙恩表态支持“红联”,被捧为革命领导干部,成为道县党政大权的第一把手。熊丙恩打倒了石秀华之后,就在道县的党政机关中来了一个大换血。他自己亲自担任道县文革小组组长,县生产指挥领导小组组长,县贫协会主席这三个职务,其余部门大小头目,全部安插自己的亲信和“红联”的头目担任。于是,熊成了这座山区小县的太上皇,他一跺脚,道县就会地动山摇。1967年2月以后,道县的群众组织围绕着“保石反熊”还是“保熊反石”问题,形成“保熊反石”的“红联”派和“保石反熊”的“革联”派。“革联”得到县城多数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支持,“红联”得到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县人武部的支持,因此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的支持。熊炳恩在军管后出任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
随着对二月逆流的批判和给“湘江风雷”的平反,道县部分群众组织中出现了对熊丙恩二月上台的质疑,有人甚至提出了石秀华的问题。熊丙恩感到焦虑和恐惧,他知道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自己的宝座就会在一夜之间颠倒过来。零陵地区,衡阳地区好几个二月份成立的新政权,就是这样垮掉了。
于是,他以县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召集各地区和各公社党委负责人会议,提出将原来的“贫协”改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八月十日,熊在县委新楼召集“法院”头头开会,会上他说:“现在上面瘫痪了,我们不能耽误。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再迟疑我们*人就会像四十年前在武汉长沙那样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1967年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湘江风雷”被打成“反动组织”。县人武部在镇压“湘江风雷”同时,对“革联”派以大力打压。“湘江风雷”在5月以后又重新复出,并与“革联”联合反熊。“革联”派在县城得到发展。
5月以后,两派不断发生武斗,6月以后,开始在县城和郊区进行派性武装割据。随即,双方的武斗规模不断扩大。在“你死我活”的武斗中,两派都在标榜本派的革命性,编排对方的罪名,以致其于死地,消灭对立派。
8月5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负责人参加的“全县抓革命促生产”紧急会议。熊炳恩在作会议总结时,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提出: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罪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熊炳恩是要为在日益紧张的派性斗争中,找将对立派和“四类分子”一视同仁进行镇压的借口。会议号召全县狠抓阶级斗争并严厉打击四类分子。而各区、社负责人回去后很快就掀起了大屠杀高潮。
8月8日,道县“革联”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抢夺了武装部的库存抢支蛋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抢支蛋药全部抢走。“八•八”抢枪后,“革联”用抢来的武器,迅速装备其武斗队伍。其势力在道县县城大张。
8月9日,“红联”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红联”的失势使得熊炳恩感到紧张。他提出“革联”的行动,是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向新生革命政权的猖狂进攻。因此,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杀人运动。
8月10日,熊在县委新楼召集“法院”头头开会,会上他说:“现在上面瘫痪了,我们不能耽误。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再迟疑我们□□人就会像四十年前在武汉长沙那样被□□反动派屠杀。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在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47军转发了这份电报。电报称∶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
军队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77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8月11日晚上,“红联”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枪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会上强调,必须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
与此同时,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召开全县各区、社“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栽红薯任务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从而确定了以“打击阶级敌人”为名,针对“革联”派和“四类分子”的镇压运动,在道县开始发动起一场大屠杀。
8月13日,“红联”进攻道县二中的“革联”总部的战斗失利,被打死2人,打伤多人。“红联”举行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而“革联”派大有实力,手中有枪,占据了武装割据的地盘,又有造反派的名头,有力量击退“红联”派的进攻和屠杀。至于那些身份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阶级敌人”,在毫无反抗能力和可能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做了道县大屠杀的刀下之鬼。当日,熊炳恩对四马桥的王甫昌、一区的武装部长刘善厚、七区副区长宛礼甫,以及由县里派去大坪铺的张望耻和其他各区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负责人说:“告诉下边,一队可以先杀一两个。”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陈智希的指示,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决定“搞掉”历史反革命分子、曾经当过军统特务的朱勉。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
当晚,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召集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山上,将朱勉打死。朱勉成为道县大屠杀第一个被害人。从此,道县大屠杀迅速发动和开展起来。
8月13日,祥霖铺区的宛礼甫在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杀掉了7人。紧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百人杀人团,分赴各个公社和大队,组织更大规模的屠杀。被杀的有的是从床上拖起来的,有的是从田里叫上来的。从8月13日到8月底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据宛礼甫上报的杀人名单中,一共杀掉了一千多人。
在四马桥区“红联”副司令、杨家公社公社“红联”司令蒋文明的策划和指示下,8月15日晚上,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主持召开召开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又以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要“组织反革命暴动”,“杀害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罪名,杀害了钟佩英和她的两个儿子。
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支书、大队长、治保主任、民兵营长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31人。
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召开清塘区生产队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主持。在会上,他强调: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从八月八日抢了武装部的抢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8月13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我们区也发现了“农民党”和“新民党”,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向与会者布置杀人任务,并要求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行使生杀大权。
久隹、新塘两个公社的5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4天内杀了13人。凤成洞、中文洞大队杀了四十多人,当数字报给熊丙恩时,他顿时凶相毕露,厉声斥责道:“你们那里就那么清白?你们的阶级立场到那里去了?”于是,这些地区的干部为了保住自身的平安,只好回去补杀人课。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时间共杀人1054人,全区50人中就杀了1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8月22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即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5人。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同时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5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囗,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
同日,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囗,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当晚,王盛光打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要他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
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到8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但小甲大队行动不力,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几次向该大队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
8月30日,杨盛芳和杨盛芳和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抢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当天,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将这12人坐“土飞机”炸死。
8月23日,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先后共开庭审讯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公社武装部长敬反修、公社贫协副主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梁域指示下,27日,艳旗大队杀7人,28日,红旗大队杀6人。
8月29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传达解放军47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但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讲话,却表扬了那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15人。会后,梁域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决定,当晚杀掉了朱用进父子等4人。
8月2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将各个生产队推出的21名青壮年“四类分子”五花大绑,由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民兵和积极分子押解至葫芦岩的洞囗,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这些人的死刑。他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囗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有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在洞囗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稻草,点燃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内重归寂静。
随后,何兴盛回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和公社汇报请示。得到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全部杀掉”,公社党委书记“一个个都给我搞掉!”的指示后,当晚,何兴盛指挥民兵,将31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
道县杀人的消息传到长沙,当时的省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同支左的47军派出刘兆丰副参谋长于8月30日,赶赴道县,召开各区各公社干部会议,宣布命令停止杀人,敦促他们立即赶回去制止屠杀。熊丙恩在散会之后示意这些干部故意在路上拖延时间,有的甚至在路上打电话通知刽子手抓紧时间,在一天内把该杀的人杀光。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三天内共杀569人。
9月1日清晨,47军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部队两次向广州军区和□□、国务院报告,提出制止杀人的措施。9月22日,经中央批复,6900部队和湖南省革筹小组向零陵军分区发出电报:“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杀人,对组织杀人头头要严加追查,对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必须坚决取缔”,发出严禁打砸抢抄杀的通告,并用飞机将电报和通告在道县撒播。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至10月25日,零陵地区杀人风潮被制止。
道县阎维胜、周志清、蒋良信、何适、王恩昌、周家丰、周贤维、刘香喜等8人,冒着生命危险,走访了一百多名当事人和目击者,走遍了道县的村村落落,含着热泪听那些孤儿寡母叙述他们亲人惨遭杀害的经过。最后写出了道县屠杀经过大事纪三百多页,记录了有名有姓的六千多名死者的全部材料。前后半年,用多种方式向湖南省委汇报,控诉熊丙恩等人的罪行。
中央着令湖南省委调查上报,湖南省委又批转零陵地区,零陵地区又批转道县县委。材料就象一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最后又回到了被告熊丙恩手上。熊丙恩和道县县委向零陵地区报告:死人是实,是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时被打死的。零陵转报省委,省委再转报中央,皮球按照原来的路线又转了一圈。一个圈的时间是整整一年。
而8名上书者则遭到程度不同的残酷迫害:阎维胜,因为姓阎,又是北方人,被扣了一顶阎西山特务的帽子,关押了一年,在监狱里受尽了毒打和折磨。周贤维、周家丰两人,曾任大屠杀专案调查组副组长,被长期关在牢里,先后受迫害死亡。蒋良信,则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10年。刘香喜,被判死刑,后改为20年徒刑,在牢中被打得死去活来。历史应永志他们的英名。
如今,这三百余页材料的八名作者半数已作古。这篇文章是对六千五百名冤魂的悼念,也是对八名作者的淡远安慰。
但也有人认为,对永州道县这样有组织的无辜杀害近万人的大规模集体屠杀,红卫兵的“打、砸、抢、抄、抓”,也没有单方面地揭露造反派的“文攻武卫”。其揭露的对象,恰恰是党内走资派及其倚为保护的保守派。
就全国而言,文革中的武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期的一般武斗阶段和后期的“全面内战”阶段。第一阶段起于“白色恐怖”的五十多天,迄于1967年4、5月。这一时期有个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据此,造反派也有一句口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这既表明了造反派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立场,从中也可看出当时人们对于武斗的最初理解,只是限于抓人、关押、捆绑、吊打、罚跪等一类“触及皮肉”的暴力。因为文革中最初的武斗,是在刘邓工作组支持下,一些以“红五类”自居的“八旗子弟”搞起来的。他们一开始就背离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对准一些有出身和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黑五类”以及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造反派,对这些被他们称之为“阶级敌人”的人施以抓人、关押、捆绑、吊打、罚跪之类的暴力“斗争”。1966年8月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工作组如鸟兽散,这些“八旗子弟”又组织什么“西纠”、“联动”之类的组织,专事抓人、关押、捆绑、吊打、罚跪之类的破坏性武斗。虽然如此,这一阶段武斗加害的对象,基本上都是无法武力反抗的个人,而不是有组织的群体。加害方也基本上处于随心所欲的绝对权威的地位。文革后,你也起来控诉文革如何受迫害,他也起来控诉文革如何遭武斗,其实很多迫害和武斗都发生在这一阶段,都是各级大大小小的“八旗子弟”所为。一些文革初期遭受武斗的知识分子尤其叫人难以理解,他们理应控诉迫害他们的“八旗子弟”及其“老子”才对,反过来却追随当初的仇人一起妖魔化毛泽东、文革、造反派,不知良心到哪里去了。当然,这一阶段也不排除造反派起来后,对曾经触及过自己皮肉的人进行过报复性触及皮肉。应当说这是造反派所犯的一大错误。
第二阶段的“全面内战”是由第一阶段的一般武斗升级而来的。随着“西纠”、“联动”一类子弟军的迅速瓦解,走资派们再也沉不住气了,1967年2月,他们撇开已经败下阵来的子弟,亲自出马,掀起了一股凶猛的“二月逆流”,再次使用武力,将造反派重新打了下去。结果是激起了全国性的反击“二月逆流”高潮,他们于是又策动了新一轮的武斗,从1967年4、5月起,开始大规模挑动农民进城围剿造反派,迫使各地造反派纷纷拿起武器,实行“文攻武卫”。从这时起,一般武斗便开始升级为“全面内战”。1967年7月以后,随着中央对各省市的明确表态,走资派感到大势已去,反抗因而愈加疯狂,干脆动用枪炮坦克,更是将“全面内战”升级到了现代化战争的水平。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场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三、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




